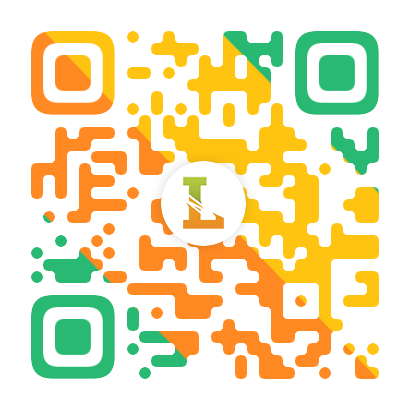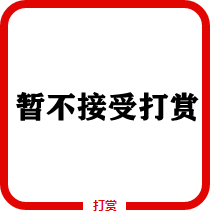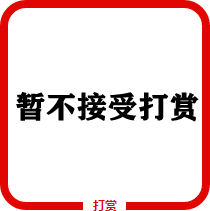画家范宽励志名言

匠人心刀剑梦散文
“三剑客”的江湖
蓉城深处,宽窄巷旁,溪山工作室隐匿于此。推开工作室厚重的木门,入鼻的是瓶插腊梅的淡雅馨香,乾隆贯霄剑、金刚杵法剑、唐金银平脱横剑、乾隆御用阅兵大刀……这些曾在历史长河中威名显赫的刀剑,静谧地躺在展室两侧,在灯光的柔和映衬下,闪耀着鎏金光芒。
说起这些耗费数年心力精心复制出来的刀剑,龚剑和李永开便根本停不下来,一如天真烂漫的孩子骄傲地分享钟爱的玩具。
李永开就像是三人中的“带头大哥”。在成都开间广告设计公司,做得顺风顺水。
何伦涛是李永开的老友,做过金融、投资和设计公司。认识李永开后,两人经常相约去送仙桥古玩市场,在这里,李永开打出了第一把刀。“现在看来,那完全就不能叫作刀,但却满足了我对刀剑最原始的乐趣。”直到遇上龚剑,李永开心里的这颗种子才真正开出花朵。
或许是名字里有个“剑”字,冥冥之中,刀剑在龚剑眼里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始吸引力。2000年左右,龚剑在四川甘孜州工作,跟藏区有了很深的接触。“那里地广人稀,也没有其他娱乐,我就经常看当地老乡收集的藏刀,慢慢也开始自己收集。因为下手早,莫名其妙收了很多有特点、非常古老的藏刀。”直到很多年后,网络论坛开始流行,龚剑才发现原来还有一群和自己有着同样喜好的人。为了更好地收兵器,龚剑干脆就在成都的送仙桥古玩市场开了个古董铺子,成了一名闲散的古董商人。
就这样,三个来自不同领域,此前干着不同营生的男人,成立了一家“溪山”传统文化机构,名字,最典型的,就是补酒坛和铁锅的匠人,这些手艺似乎也有一定的集群关系,比如有些村子是专门弹棉花的(如屏南的忠洋村),有些是打银的,补缸的师傅,大多来自周宁一带,挑着工具担,用周宁话拉着长调子,沿街巷一路喊着:“补—缸—补鼎哟……”有需要的人家,就出门来招呼,师傅就放下挑子,在门边的路边,支起灶具开始干活,周边的人家有东西要补的,就一起聚拢过来。也有的师傅,直接在街边上固定一个地方干活。那时,补得比较多的除了缸和锅,就是塘瓷杯盆,常常是圆形底边上大大小小补着几个眼。师傅把漏的孔眼周边,用锉刀等工具清理干净,剪个合适的金属片,把漏孔的地方堵上。补漏的材料用锡,连着手拉风箱的木炭炉子上,一个拳头大小的陶土器皿烧得通红,里面锡化成水状。准备工作都完成后,师傅根据孔眼的大小,把合适量的锡水,倒在一撮草木灰上,草木灰的下面垫块破布或瓦片,师傅的右手伸进杯盆内侧,用布把垫在里面的金属片扶住,左手拿起锡水,迅速往孔眼处按压,使锡水很快粘住孔眼,并渗入内侧将金属片牢牢粘住。补鼎的工艺类似,只是工作量大些,要沿锅的裂隙扩大创面后,码上一排的如瓜籽大小的梭形金属片。补缸的工艺稍不同,得用上铆钉,像补衣服一样,用铆钉沿缝隙钉一排。
银匠、铜匠、铁匠
银匠和铜匠手艺类似,但又有区别,银匠在我们老家土话叫“打银人”,差不多就是做首饰的。村里有个长驻的银匠,好像不是本地人,在老街上不同房子里长期租住过,秃顶、近视又耳背,做事时,总是戴着一副拴着绳子的厚眼镜,他手艺很好,据说也很有钱,但十分节俭,也一直没有娶到老婆。俗话“打铜仔”就是铜匠,业务类别好像比银匠更多些,有做铜器,锡器等,也有一部分补缸补鼎工作。铜匠多数是流动的摊,或到别村找个东家住下,定点做一段时间再换个村,如此轮回。铁匠就必需定点了,印象中,铁匠铺都是破烂不堪,黑乎乎的,烟熏火燎,不会引人驻足观看,过路时,只听见一阵阵时缓时急的锤打声,和拉风箱的呼噜声。
弹棉匠
我们村没有会弹棉花的,大多从忠洋村一带过来,弹棉匠最典型的,就是工作时的那身装扮,背脊上竖着一根竹杆,大的一头用腰带固定在腰间,另一头向前弯曲,末端垂下一根绳子,一个两米来长,状如巨大的琴弓一样的工具挂在绳子上,悬在师傅齐腰边,琴弦是一根很粗的牛筯绳,师傅左手握住弓形杆的中间(也是绑绳的位置),右手拿着一个如啤酒瓶状的锤子,不停地拔着琴弦,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靠牛筯弦的抖动,把成团的棉花弹成丝丝缕缕,然后把棉花摊成棉被大小,织上棉线,有的还用有色棉线,织上图案或喜字,再用两个像锅盖一样的大木轮把棉压实。一天下来,师傅身上头上都沾满了碎棉絮,像下了雪一样。一般师徒二人,一天就做一床棉被,只包工不包料,按如今的工时成本算,是很贵的了,工匠时代,在效率上是远不能和现在相比的。
石匠
现在城市建楼打地基不用石头,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水泥没有普及的时代,地基石材是必备的,建房首先要请的就是打石头师傅,除了石雕师傅外,,石匠大体上分为釆石师傅和做地基的师傅,工种稍不同,也有二者都会的。釆石师傅主要上山采石,机器设备没有普及前,除爆破外的其它工序全靠手工,爆破下来的大石料,他们靠简单的钢钻铁锤,通过成排的钻眼,把石头崩裂成合适的大小,看似很粗的力气活,其实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要让不规则的大石头,沿预设的方向崩裂,是需要经验和技巧的,高明的师傅,才能规整地崩切石条,断面平整,甚至直接就能当成品用。垒地基的师傅似乎省力些,只需对石料做简单处理,因材施用,但要让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块间,相互契合承受整墙的重量,是十分考验师傅功力的。很多乡村的地基,是就地取材用鹅卵石砌成,技术十分了得!
我家镇上有个叫乃佑的前峭村,那个石师傅我稍了解,考溪村建小学时,就是请他做的地基,他是我父亲在前峭教书时的学生,学习似乎不怎么样,但豁达机灵。他父亲是石匠,并不想让他再学这手艺,可他自己喜欢,父亲做事时他就看着,有一次他按耐不住,径自上去垒了七八块石头,问父亲做得如何,他父亲看他做得有模有样,嘴上虽不说,心里却十分赞叹,从此也不再反对,慢慢教他,后来他就靠这门手艺生活。
裁缝
我对门邻居叔婶两口子,就是做裁缝的,靠这手艺赚一家人的饭食,生活在当时已达小康,还把6个孩子中的5个,培养成大学生(他一家9个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很不容易,在村里传为佳话),现在传统裁缝的生存空间已经很小了,他在九十年代初就不做了。后来,开了一段时间的食杂店,十几二十年前,街上还有不多的几间裁缝店,如今也多数换了别的店了,老街上只有一间还继续营业,是我一个亲戚开的,我叫她表婶,她家算是世代的传承,我小时候,家里难得做的几件衣服,几乎都是她做的,做衣服用的布和扣子之类,都是自已去布店里买的,量了一下身高腰围,就按师傅的做下去了,至于样式,压根就没概念,印象中,多是中山装类似的结构。现在的主要业务,是做寿衣和帘子之类的活,很少有人做衣服了,用的还是老式的脚踩缝纫机。
剃头匠
理发这行当,只要人存在,一天就不会灭绝,不仅没有成为非遗,而且现代文明进步,把这个行当从内容到形式,都发挥到了极至,但如何机械化,总还是师傅技术为主。我小时候,村里理发师傅基本都是老头子在自家为人理发,专业开理发店的,只有阿丁一家,他也兼修表。理发的客人也都是男性,女性头发似乎都是自已剪或结辫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记得最初是因为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流行烫卷发,就慢慢有了女理发师,阿丁的几个女儿,也跟父亲学理发了,越来越多的女人进店做头发,后面花样就越来越多,从客户对象到从业人员,再到设施工具、业务类别都革命性地改变,如今理发店里,已是街面上帅哥靓妹集合最扎眼的处所了。
道师
老家有一种像道士一样的.师傅,村民称为“先生”,专为人们做法事的,归为匠人有点牵强,这里也权当一门手艺来说吧,他们最经常的,是给小孩“过关”、“招魂”,或给死去的人超度,也给人们择黄道吉日,算是村里必不可少的一个行当,在外人看来,也是十分玄秘的,小孩们对这些“先生”都很害怕,平日里都敬而远之,大约因为见了他们,就想到死人的缘故。我邻居就有一位这样的先生。他的房子和我家隔一条窄巷,很破,摇摇欲坠的,门上,外墙壁上歪歪斜斜地钉着旧木板,总是贴满了各色的纸符,他也许用这办法防止房子倒掉。我父亲和他很要好,小时候,父亲带我去他家玩过,吃过他的不少东西。他活儿多的时候,有时叫父亲帮他写疏(一种与神灵沟通的文书,像信件一样,做法事时,要烧了让神明收去)。这是一个不亚于其它匠人的专业活儿,得有正宗的传承,比如从父辈或师傅传下来,礼仪规矩十分讲究,不能马虎,文书格式都十分严格,做法事时,有一整套类似咒语的唱词,听着喑哑浑浊,模模糊糊的,但是,一招一式极其庄重。
这活儿现在几乎要成为非遗了,原先,我们村里有三位这样的先生,如今都已去世,似乎也没有合适的人传下来,另一方面,现在基督教影响也越大,他们不做这类法事,“市场”也就小了很多。年轻人更是觉得无利可图,不愿去学了,据说,现在有这方便需求的,都得到邻村去请。
劁猪匠
这算是极冷僻的一门手艺了,我如今都差点没记忆了。小时候,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只记得小猪买回来养不多大时,就会请劁猪师傅来家里把猪劁一下,也就是阉猪。这算是一项觉得残忍的活儿,小时候大人开玩笑吓小孩就说:“再调皮!把你小鸡鸡劁了……”小孩们就识趣地用手护着裤档慌乱逃去,大人哈哈大笑。记忆中,村里只有一人会这手艺,人家叫他“阿忠师”,是我一个女同学的爸爸,壮实,上身长下身短的样子,走路摇摆起来一副威武样,传说他会武功,不知真有其事否。他劁猪只带很简单的工具,一把刀,一根带着短棍的绳圈。他身手敏捷,户主把猪从栏里赶出,趁其不备,一把拉住猪后腿,猪倒地瞬间,他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捆挷了猪的脚,同时用套索套住猪的嘴,猪就是剩了叫的份儿了,他娴熟地取出刀具,割开猪后腹某个部位,伸进两手指往里掏了一小会儿,抠出一小撮像菜花一样的东西(大约是猪的卵巢),然后用针把创口缝上,涂上点锅底黑灰,就算完事了,前后不到10分钟。
360行都有工匠,如今,各行各业分工细化,其实,工匠的类别是更多了,减少的只是传统的工匠,现在还较常见的传统工匠,大约是补鞋匠,磨刀匠之类,高大上一点的有木雕根雕匠,更多的类别,我们这一代已经很模糊了,上面是我比较熟悉,而现在又很少见的几个类别。记得小时候,还有一种专门给嫁妆画“厨花”和专画老人像的画匠,我母亲陪嫁的衣柜门上都画着厨花,用油彩在玻璃或木板上画各色的花卉、风景,人物故事等,十分逼真,我在乡下的时候,也当了业余画匠,给人家画了一些老人像,我见过我曾祖父的画像,应是民国时期所画,彩色的,非常细腻逼真!功夫是我的百倍以上,如今这行当,已被照相技术彻底取代。
印象中,乡间的手艺人都是平平实实,千百年来延袭传承,靠手艺赚口饭食,养一家人,平时大多也种地,与普通的农民没有太大区别,大多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勤快点的可小康,因手艺而大富大贵的很少,乡间似乎也没有暴富的环境,即便是如今的产业技师,要大富大贵也并不容易,甚至收入远不如销售人员、中介商或投资客,但这些默默的工匠,才是真正推动技术进步的。
如今工匠的概念,己大大减弱了,但广义上的工匠,永远不会消亡,仍会以产业技师的形态存在,我们只是和他们之间隔了一层市场而已。现在生产高度集约化,大到建房,小到生子,用品基本一站搞定,省时省力,也品类齐全,大大方便,但相应地也缺了那些过程的乐趣,机器味重了,人味也就淡了。时下热烈讨论人工智能胜过人脑,机器人控制人类,机器人战争……我并不以为,在创造性上人工智能真能胜过人脑,但像手艺这种局部技术领域,机器是早就超越了人类了。如今我们都已习惯认品牌,认不出也用不着认是哪个师傅做的了,造价、款式、效率比工匠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百姓也相应地随意起来,对工匠的敬重,也大不如前却挑剔有加。如今,乡村各类物件也都趋向泛滥,垃圾大量产生,环境和水质都大大下降,工匠时代的物件大都少而精,当今是丰而杂,有利必有弊啊!
梦越是美好,就越让人心碎散文
“没事,有我在你身边呢。”脑海中残留了这么一句话就猛地从梦中惊醒。终究只是梦。就连不舍与依恋都狠狠地立马折断。
睁开眼睛才发现原来天早已白亮,之前的黑暗都只是因为自己闭上了眼睛。有些沮丧地从身旁一天皱巴巴地被单下抽出闹钟,迷糊着双眼喵了喵。凌晨5:57。若在冬天,这恐怕还是一片的漆黑的,可是,毕竟是夏天。而且盛夏的白昼总是来得太早,去的太晚。已经无心再继续睡,胸口像是强迫性地塞进一团棉花,堵得发慌。于是便索性纵容了自己爬出平日依恋的床。
窗帘在落地窗前投下一片暗影,像光亮的白昼里怎么都拂不去的黑暗。风偶尔调皮地缓缓掀起轻盈的帘布,但又迅速地落下,固执地守着那一片投影的暗黑。怀缀着沉甸甸的的.心事跨过帘布的暗走到了窗台上,想就此让心事呼吸下早晨的新鲜的空气。雨后的清晨,空气中夹杂着一抹濡湿,绵绵的黏黏的,像夏天惹人憎恨的汗液,但是又不同于汗液。它的绵绵黏黏中又裹藏着清爽,令人不得不爱上这美妙的早晨。万物都还在沉睡,只有勤劳的蝉早早地醒来高歌。树梢上,轰轰的一片略带嘈杂地鸣叫,将安静的清晨撕毁地只剩下一片清新。
“没事,有我在。”简短的一句话,像魔咒般刻在了心里。如果这真是魔咒,那什么才是真正解开魔咒的钥匙?
散文之罗儿匠的传说
“你舅爷被土匪活活烧死了。”娘忧伤的念叨着,一边“哧啦、哧啦”地纳着鞋底。
冬日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热呼呼的土炕上,一盏小灯泡晕出一片黄光。父亲举着一尺多长的烟锅,慢悠悠地有一口没一口地品着旱烟。姐姐看着连环画,弟弟缠着娘讲故事。娘在生产队劳累了一天,一边做着针线一边悠悠地讲述起外婆家的陈年往事。
外婆家是我们那一片有名的大财主,人称“罗儿匠”。因为他家在高店镇开了一家加工销售蒸笼、罗儿的门店。
高店镇是关中渭水南岸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相传在三国时诸葛亮的前锋大将魏延在此驻扎,与魏国大将司马懿隔河对峙,史称“魏延城”。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高店镇就演变成渭水南岸一个大的集镇,辐射宝鸡、眉县、周至、太白等县,解放前主要交易山货木材、粮食农具、家禽牲畜。老街南北走向,青石铺路,十几家店铺,分列两侧。每逢农历单日,人们肩扛担挑,挎篮推车,上街跟集。人流熙熙攘攘,生意兴旺发达。
外婆家的罗笼店在街道南头西侧,是一座三开间的青砖瓦房,门前几棵土槐如伞如盖,浓荫蔽天;台阶用丈余方方正正的石条砌成,店门是一排红色铺板,可拆卸安装;门两侧一对石狮,双眼突出,口衔石珠,威风凛凛。走进店铺,红色的木头柜台上,摆着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蒸笼,笼圈用筷子厚的薄板做成,笼底是一排青绿色的竹板,有圆有方,有大有小,结实耐用。四周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罗儿,有布底罗儿、蚕丝底罗儿,还有铜丝底罗儿,琳琅满目。店后是罗笼加工场,叮叮当当,一派繁忙。木工拉锯刨板,烤炙笼圈;竹匠劈竹划篾,捆扎笼底;几台织机梭子飞舞,银线穿错,哐哐哐地织着罗底。
解放前,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几乎每家都有一台石磨子,粮食收拾干净,套上一头小毛驴或一头黄牛,孩子“嘁得、嘁得”地赶着牲口,拉着磨子吱扭扭地转,磨碎的粮食“簌簌簌”的流下磨圈,女主人头上顶一块白布,地上放个大蒲篮,用两根棍子架着罗儿,撮一小簸箕磨碎的粮食,倒入罗儿,哐当哐当地罗出雪白的面粉。一天最多磨二斗粮食。
北方不产大米,最爱吃的就是馒头、面条,三五天就要蒸一锅。罗儿、蒸笼就成了农村必须的生活工具。
外婆家经营着店铺,家里有几十亩旱地,槽上一群牛马,舅爷却特别节俭。夏天,舅爷总是光着膀子,下身穿一条过膝长的裤子,腰里系一条布带子,脱光头发的头上扣一顶破草帽,天不明就领着家人下地干活,浑身晒得黑红黑红,一年四季没闲过。家里姑娘媳妇上灶做饭,晴天做干饭,雨天喝稀饭,吃饭时干活的人吃完,才轮到妇女小孩吃。
树大招风,外婆家滋润的日子也招惹了不少人眼红。
解放前夕的关中农村,匪患严重,民不聊生。外婆家几次遭土匪抢劫。舅爷在家里建了座防备土匪的“楼子”。楼子是一座四方塔型的土木建筑,四周黄土夯实,木柱横梁结构,三层高,远望像一座大烟囱。每层一架木梯,两个盆口大的窗户,用来通气、透光、喊人,一个半尺厚的磨扇盖着入口。发现土匪抢劫,一家人就躲到楼子上,老人妇女儿童上三楼,青壮年在二楼防守,楼上备有土枪和砖石瓦块,以防不时之需。我小的时候,与弟妹捉迷藏,还常常爬上楼子玩耍。
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一个土匪趁天黑之际偷偷溜进并藏在外婆家大院里,等家人睡熟之后打开大门,其他土匪一涌而进。所谓“土匪”也就是农村一些游手好闲之徒,馋嘴懒身子,干活怕出力,或沾染大烟毒瘾,或耍钱失光了房屋土地,媳妇跑了,吃了上顿无下顿,纠集在一起,冒险抢劫富人。
这群“土匪”共5人,头用围巾裹得严严实实,漏出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鞋露脚趾,夹着条单裤,棉袄开了花儿,腰里系条草绳,手拿土枪或大刀。土匪把全家十几口人赶到了大厅,威胁不给钱就杀了全家。
舅爷哆嗦着说,掌柜的,快坐,给你们做饭。
大个子土匪“哐”的一声,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供桌上,少啰嗦,快拿钱!
舅爷拿出一堆国民党时期的纸币“金圆券”,被大个子一把打在地下,少拿这个糊弄,快取“袁大头”。
掌柜的,兵慌马乱的,哪有“袁大头”呀,楼上粮食你们装,槽上骡子你们牵,保佑我家平安。
那时已临近解放,胡宗南和“二马”的军队,负隅顽抗,在扶风、眉县一带布防,占领渭河两岸有利地形,妄图阻止解放军西进南下。晚上偶尔响起一阵枪声,有时,诸葛亮庙跑来几个逃兵,快割麦子的季节了,还穿着棉衣棉裤,自己坐在庙前戏台下,拆掉棉花,做成单衣穿上,向山区逃窜。戏台前后到处是破衣服、烂棉花、臭袜子。
人心慌慌,大姑娘小媳妇晚上不敢呆在家,风声紧时,整晚蹲在麦地里。娘还没有出嫁,外婆领到我家说,兵荒马乱,你家媳妇自己管吧。娘一辈子都后悔,结婚时没有办个体体面面的婚礼。
拿土枪的小个子暴躁地挥着抢,老东西不见棺材不落泪,给我吊起来!舅爷被五花大绑,吊在了房梁上。
男人们浑身发抖,女人们哭出了声音。
土匪用鞭子抽着舅爷,舅爷鞋子掉在了地上,光着两只脚,断断续续地说,粮食……骡子……你们随便拿……
土匪一边打一边在家里乱翻东西。打了一个时辰,实在找不到银元,一个土匪看到墙边放着几老瓮菜籽油,从旁边织布机上拿来2个线穗子,蘸上菜油,甩在舅爷的胸部,点燃了线穗子。
线穗子呼呼呼的燃烧着,舅爷在房梁上声嘶力竭地嘶吼着,家里人齐嚓嚓地跪下求着土匪。
正在这时,稀稀拉拉的枪声从诸葛庙方向传来,由远而近。小个子土匪趴在大个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大个子恶狠狠地吼着,老东西,算你狠!大个子叫手下找来一把扫院子的大扫把,伸到油瓮里蘸了一下,放到舅爷的脚下,点燃了扫把。扫把哔哔啵啵的燃烧着,燃烧着舅爷的衣服,燃烧着舅爷的全身,舅爷无力地耷拉着头,在房梁上无声地挣扎着。
枪声越来越近,土匪们才匆匆忙忙地夺门而逃。
后来听说有人报信,镇公所的保安队来了。
土匪跑了,家人才七手八脚地把舅爷解救下来,请大夫救治。舅爷奄奄一息地在炕上睡了几天,就去世了。
过了几年,外婆家家道中落,连罗笼店也散摊了。但一提起“罗儿匠”,老人们还会津津乐道地谈论起“罗儿匠”的兴衰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