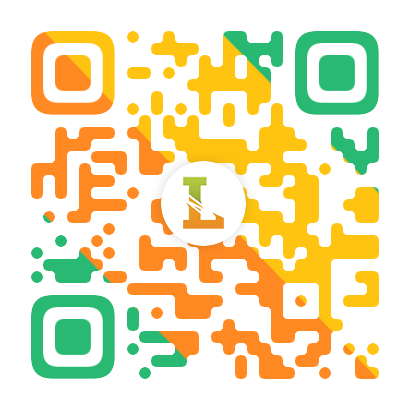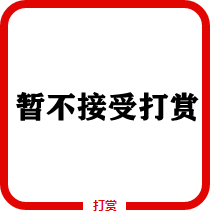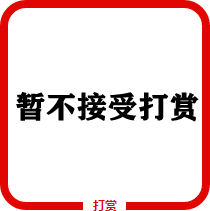汪曾琪的名人名言

祁白水是日照文化学者,他在《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的名家侧影设有专栏。而我又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想从现代名家学起的人。白水老师从侧面介绍名家,我就从正面学习名家。一侧一正,就全面了。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岂不两全其美。慢慢地,我就形成了无法改变的习惯。
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先后跟着白水老师学习了流沙河、何立伟、阿城、王兆军、刘玉堂、赵德发、鲁迅、汪曾祺、周作人、孙犁等现代当代名家的诸多作品。而让我最感兴趣投入全部精力最深入学习的有鲁迅的杂文、赵德发的小说,还有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老先生在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美食、书法等方面皆有较高造诣。他的作品大多数是谈饮食,谈草木,谈文化,谈民俗,谈花鸟虫鱼、叙师生情,写凡人琐事,雅俗共赏,有着“士大夫的趣味,平民的情怀”。
汪老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深神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说过:我希望把散文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老的散文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说话,虽百事杂陈,但饶有兴味。
汪老在《蒲桥集》自序上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常常道:我是歪才,善能胡诌。
他善于以个人的细小琐屑生活为背景,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他善于以平实委婉而富有弹性的语言,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抨击了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名士风散文的魅力。汪老的文学主张让真善美来自生活,恬淡和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局面,功不可没。
他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写出来的文章却发人深思。他的作品无论是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再到花草虫鱼,瓜果食物,无所不涉,都能信手拈来。文如其人,源于汪老心境的淡泊和他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情释然。
喜欢汪曾祺就要多读他的作品,先去了解他的家世。汪老的祖父是清朝末期的拔贡,拔贡就是可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祖父文章写得很好,喜欢收藏古董字画。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祖父就是很有名的眼科医生,开了两家药店,信儒学佛。汪曾祺的父亲是温尔文雅、恬然随和的人,很少见他发脾气,从来不对子女疾言厉色的。他是画家,画写意花卉,会刻图章,初宗浙派,更喜欢藏石。父亲是心灵手巧的人,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所不通。
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学生。他的创作风格是受沈从文影响的。他俩都是小说见长,善于写人状物,善于把自己的情感深藏在人和事之中,具有天然的随机性。小说创作“要贴着人物走”,小说里人物才是主要的、主导的,不能离开人物去抒情、发议论。所写之景,既是作者之景,也是人物之景,也就是“气氛就是人物”。还有两个人对话越平常,越简单越好。
汪老曾说:我是极为平常的人,我没有深奥独特的思想。我写的小说都是平常事、普通人、小人物,因为我对这些人和事比较熟悉。什么是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地写出自己所看到的生活,不要搞得太复杂。想象和虚构的扔到河里,觉得很可惜。于是,他把牛杂捡回洗净后,放在有中草药的汤锅。结果发现熬出来的汤味甚是鲜香。因味特汤香,又有防病治病的'功效。所以,特意来饮者络绎不绝,堂堂爆满。其间没有席位者,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就直接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跷着二郎腿端碗即食。久而久之食客们便形象的起了一个“跷脚”牛肉的别称,且流传至今。难怪当初在巷中小店,当地人聚餐一人一盆翘脚牛肉,也无他菜就呼哧呼哧的吃了起来,期间大汗淋漓、姿态各异,原有此故。
汪先生写峨眉山,写的是清音阁到洪椿坪的美景,一边是山一边是水,水穿石而过,飞鸟驻足,风景极好。我们也去了峨眉,路上风景虽美,但因是自驾,一路匆匆,未曾驻足,不能得见这种山水间蒙蒙耳耳的形态。但好在赶车时候肚子饿了,停下车来随意寻了一家农家小店,一人来了一碗豆花。这豆花点的不硬不软刚刚好,摆在碗中一大块一大块的,筷子刚好夹得起来,闻到的是满满豆香。配上葱花、蒜泥、香油、椒油、萝卜丁或者别的咸菜,一口下去,清香爽口又绵软细腻,丝毫没有点豆腐的碱味,这家豆花便也成了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四川豆花。
汪先生还写了巧遇五台山来拜金顶的和尚,和尚进庙,得一百八十拜,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真心诚意,一去金顶就看见普贤和尚骑象而来,前面一行天女。而我们去峨眉山才不管有没有普贤或者天女,直奔金顶看"日出、云海、佛灯、佛光"的奇景。提前一天入住金顶的酒店,早上五点就爬起来等在金顶的山间小路上。一条小路既有长枪长炮,又有我们这种拿手机的;既有裹大衣的人,又有穿着夏装外套的年轻人,总之人山人海。不知道是我们心意不诚还是运气太差,太阳一直被层层云雾遮挡,无论怎样也不肯跳脱出来,只露出一点影子后便没了踪迹。"日出、云海、佛光、佛灯"都未尝得见,空余一点遗憾。
二、跑警报
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昆明三天两头都有飞机警报,一有警报,大家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想到飞机空袭,脑海中全是炸弹掉下来,房屋倒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的可怕场景。但在汪先生笔中,一切都是轻松随意的。他们跑警报有两个点,联大学校附近的马尾松林就是其中的一个点。一有警报,做小买卖的就把担子挑了过来,里面常见的吃食中有我www.i1766.com小时候最爱吃的麦芽糖。在那个还是凭粮票、饭票购物的年代,出街走巷的小贩丰富了我小时候的生活。每一次我在家做作业总能发现丁丁的声音。一听到这种丁丁声,我就立马扔下纸笔,冲出家门,跑到家属区院子里的空旷地带,总能看到一群小孩围着一个带帽子的小贩。而我也总会以最快速的冲到小贩面前,拽着父母过年给的零花钱递给小贩,眼巴巴的看着小贩用小铁片震下一小块麦芽糖,然后我就开心的用舌头不停的舔着麦芽糖,直到沾满了舌头、嘴唇、牙齿后,自以为不留一点痕迹的挪回家。
横断的山沟是跑警报的第二个点,这个山沟是一个天然的防空洞,即使炸弹在沟顶爆炸,弹片也不容易蹦进来,所以有人利用空闲还修了私人专用的防空洞,洞中还有两幅
三、西南联大
关于西南联大汪先生写了好几篇,写校舍、写大师、写自己,相互之间偶有重复之处,但西南联大的生活却是极让人向往。联大校区分散、条件艰苦,但课程可以随意旁听,系图书馆的书可以随便借阅无须登记。教授讲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教授之间不论长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其中着墨写了闻一多先生讲课,提及他讲课"图文并茂",画出女娲、伏羲的各种画像,口讲指画,有声有色。又提闻一多先生讲晚唐诗,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中的点画派联系起来,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将文学和画画结合起来讲,非常人所能为,难怪联大文、理、工学院的学生要穿城而听。联大多数教授对学生呢,要求也不严格,中文系的学生读书报告都不重读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因此汪先生写李贺,说别人的诗是画在白底子的画,而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赞赏。有一个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问为什么?答曰自由。是否是联大人才更多我没有考证,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个学校,有好的设施故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氛围,老师教得自由,学生学得自由,以此激发思考、激发创见。
上世纪的教学就如此开放,反观我们现在的教学体系,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先学三段式,总分或者总分总。数学就学老师教的规律,至于为什么是这个规律,怎么发现这个规律不在我们的学习范围。小伙子呢,形式上学校是灵活了许多,各种社团各种兴趣课,但从整体上、从根本上还是死记硬背的多一些。我看学而思的数学,老师就是把公式或者模型硬教给孩子,让孩子解题套公式。对于语言确实需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写,但如果一直这样过度强调记、背、算,只会固化孩子的思维,而这些固化的东西迟早会被人工智能、机器取代。所以还是希望学校、老师、家长共同努力,学数学呢不仅教公式,还可以多去研讨一下公式背后的原理,让孩子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学语文呢,不仅读课内之书,读我们国家的书,中外古今都读读,体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美。只有让他们多接触多体验,才能让孩子们学会思考、学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学会理解自己、理解世界,也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