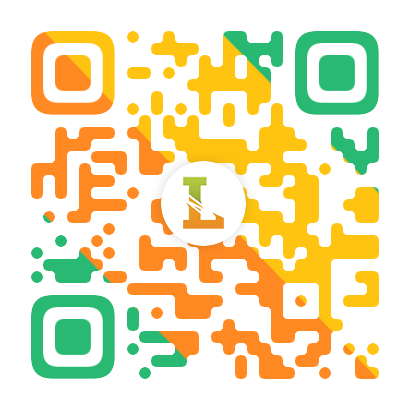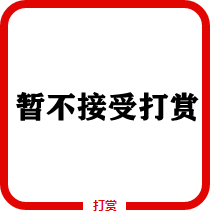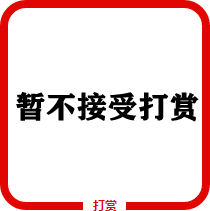汪曾祺说说我自己完整版

汪曾祺何许人也?似有耳闻。语文老师推荐的。理由?文风质朴,文笔清淡,值得好作空话、大话的“我”品味。
借来汪曾祺的散文集,略翻了翻。文章的确富有生活气息,只是,味道似乎不浓。
我只道把汪的文章搁置了下来。只是那夜,心情焦躁,疲乏不堪,我信手拿来汪的散文集,随意翻至了《西山客话》。读着读着,眉头不再紧锁,嘴里也不再抱怨了。完全被朴实文字里所描绘的迷人景致吸引住了——“山前有一片杏树,约有干株。一千棵杏树,都开了花,那可是很壮观了。远望一片浅红的海,如云蒸霞蔚,使人目眩神移。”“弄楼一侧有一棵玉兰。八大处只此一棵,据说是明代所植,高与楼齐,开花时瓣如玉片,蕊似黄鹅,一树光明。”……
原来质朴如是的文字可以描绘出如此绚烂的画面,原来用我们的'双眼可以发现如此光彩的美景。
看!汪老这样写——“西山多隐士,绝世遗名,只求执守真我。在八大处山庄怡居或小憩,做一个闲人,晨起拾级登山,暮看夕鸟投林,春花秋月,兴衰荣辱,存乎一心,然则‘清冷之状与目谋,营营之声与身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淡泊宁静,心止如泓,非但抛却都市繁嚣陆离,更能忘象见性,俨然小隐于野。”
这就是汪老的人生哲学——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恍然大悟,沉静的心也似那寂静的夜一般清澈悠远。
自那以后,我开始乐于读汪老的散文。与老人家一起品味生活,品味心情。
汪老定是个吃客,我暗想,坏笑。你看他那不滞于形的文字竟能让人垂涎欲滴。且看《豆腐》一文中——“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家常菜,家常文章,家常情调。
汪老用无华的文字回忆着一位位故人,却又那么形象而生动地呈现出富有个性的人物。看他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中有这么一段——“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
人物形象,贵在形似又神似。就在这样的文字中,我除了喜欢赵树理先生,也就更喜欢汪曾祺先生了。
汪老的散文大多如此风格,以平淡致远见长。
我想,汪老散文中的味道,浓起来了。
有人会说,家常文章,不值玩味。但我想,汪老的散文值得我们学习的恰是以下两点:其一,文字不求矫揉造作,文风平易近人,一扫靡艳之风。其二,无论作文,还是做人,都要常葆乐观从容之心态,能懂得以包容之心话“家常人生”。
这,就是我眼中的汪曾祺与他的“家常文章”啊。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阶级情况摸清楚了,群众不难发动。也不是十分紧张。每天晚上常常有农民来请我们去喝水。这里的农民有“喝水”的习惯。一把瓦壶,用一根棕绳把壶梁吊在椽子上,下面烧着稻草,大家围火而坐。水开了,就一碗一碗喝起来。同时嚼着和辣椒、柚子皮腌在一起的鬼子姜,或者生番薯片。女歌唱家非常爱吃番薯,这使农民都有点觉得奇怪。喝水的时候,我们除了了解情况,也听听他们说说闲话,说说黄鼠狼、说说果子狸,也说说老虎。他们说这一带出过一只老虎,王家梁有一个农民叫老虎在脑袋上拍了一掌,至今头皮上还留着一个虎爪的印子……
到了预定该到队部汇报的日子了,当然应该是我去。我背了挎包,就走了,一个人,准确无误地走到了夏家庄。
回来,离开夏家庄时,已经是黄昏了。不过我很有把握。我记得清清楚楚,从夏家庄一直往北,到了一排长得齐齐的,像一堵墙似的梓树前面,转弯向右,往西北方向走一截,过了一片长满杂树的较高的山包,就望见王家梁了。队部同志本来要留我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走,我说不行,我和静溶、老周说好了的,今天回去。
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青苍苍的暮色,悄悄地却又迅速地掩盖了下来。不过,好了,前面已经看到那一堵高墙似的一排梓树了。
然而,当我沿梓树向右,走上一个较高的山包,向西北一望,却看不到王家梁。前面一无所有,只有无尽的山丘。
我走错了,不是该向右,是该向左?我回到梓树前面,向左走了一截,到高处看看:没有村庄。
是我走过了头,应该在前面就转弯了?我从梓树墙前面折了回去,走了好长一段,仍然没有发现可资记认的东西。我又沿原路走向梓树。
我从梓树出发,向不同方向各走了一截,仍然找不到王家梁。
我对自己说,我迷路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除了极远的天际有一点暧昧的余光,什么也辨认不清了。
怎么办呢?
我倒还挺有主意:看来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说。我攀上一个山包,选了一棵树(不知道是什么树),爬了上去,找到一个可以倚靠的枝杈,准备就在这里过夜了。我掏出烟来,抽了一枝。借着火柴的微光,看了看四周,榛莽丛杂,落叶满山。不到一会,只听见树下面悉悉悉悉悉……,索索索索索……,不知是什么兽物窜来窜去。听声音,是一些小野兽,可能是黄鼠狼、果子狸,不是什么凶猛的大家伙。我头一次知道山野的黑夜是很不平静的。这些小兽物是不会伤害我的。但我开始感觉在这里过夜不是个事情。而且天也越来越冷了。江西的冬夜虽不似北方一样酷寒,但是早起看宿草上结着的高高的霜花,便知夜间不会很暖和。不行。我想到呼救了。
我爬下树来,两手拢在嘴边,大声地呼喊:
“喂——有人吗——?”
“喂——有人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
然而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
“喂——有人吗——?”
我听见几声狗叫。
我大踏步地,笔直地向狗叫的方向走去。
我不知道脚下走过的是什么样的树丛、山包,我走过一大片农田,田里一撮一撮干得发脆的稻桩,我跳过一条小河,笔直地,大踏步地走去。我一遇到事,没有一次像这样不慌张,这样冷静,这样有决断。我看见灯光了!
狗激烈地叫起来。
一盏马灯。马灯照出两个人。一个手里拿着梭镖(我明白,这是值夜的民兵),另一个,是把我们从夏家庄领到王家梁的小伙子!
“老汪!你!”
这是距王家梁约有五里的另一个小村子,叫顾家梁,小伙子是因事到这里来的。他正好陪我一同回去。
“走!老汪!”
到了王家梁,几个积极分子正聚在一家喝水。静溶和老周一见我进门,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们的眼睛分明写着两个字:老虎。
《卖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渊潭散步。
玉渊潭有很多钓鱼的人。他们坐在水边,瞅着水面上的飘子。难得看到有人钓到一条二三寸长的鲫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无所得。等人、钓鱼、坐牛车,这是世间“三大慢”。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这也是一种生活。
在钓鱼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见一个卖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着一辆二六的旧自行车,有时扶着车慢慢地走着。走一截,扬声吆唤:
“蚯蚓——蚯蚓来——”
“蚯蚓——蚯蚓来——”
有的钓鱼的就从水边走上堤岸,向他买。
“怎么卖。”
“一毛钱三十条。”
来买的掏出一毛钱,他就从一个原来是装油漆的小铁桶里,用手抓出三十来条,放在一小块旧报纸里,交过去。钓鱼人有时带点解嘲意味,说:
“一毛钱,玩一上午!”
有些钓鱼的人只买五分钱。
也有人要求再添几条。
“添几条就添几条,一个这东西!”
蚯蚓这东西,泥里咕叽,原也难一条一条地数得清,用北京话说,“大概其”,就得了。
这人长得很敦实,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宽厚。这人看起来是不会头疼脑热、感冒伤风的,而且不会有什么病能轻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宽宽大大的,旧的,褪了色,而且带着泥渍,但都还整齐,并不褴褛,而且单夹皮棉,按季换衣。——皮,是说他入冬以后的早晨有时穿一件出锋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了便于骑车,他总是用带子扎着裤腿。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只看到风、太阳和尘土。只有有时他剃了头,刮了脸,才看到本来的肤色。新剃的头皮是雪白的,下边是一张红脸。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旧铜器在盐酸水里刷洗了一通,刚刚拿出来一样。
因为天天见,面熟了,我们碰到了总要点点头,招呼招呼,寒暄两句。
“吃啦?”
“您溜弯儿!”
有时他在钓鱼人多的岸上把车子停下来,我们就说会子话。他说他自己:“我这人——爱聊。”
【《汪曾祺说:我的世界》推荐】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 本书始终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从他的阅读同写作,从他的交游与回忆,了解他,接近他。特别收入了八篇弥足珍贵的散佚文章,作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年的纪念。
【《汪曾祺说:我的世界》内容简介】
始终围绕着对一个作家的认识角度。从他作品里透出的感怀,从他的阅读同写作,从他的交游与回忆,了解他,接近他。特别收入了八篇弥足珍贵的散佚文章,作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年的纪念。汪曾祺是民族的。他作品的语言都是中国话。学习民间,阅读经典,并且字句讲究。
汪曾祺是继承传统的。他的历史文化学养,来自博杂深入的阅读。
汪曾祺是世界的。他对外国现代作家作品有选择地用心学习。
汪曾祺是时代的。他对自己经历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有关注。每个阶段,都有写作。他说过:“写作,是我生命全部。”
汪曾祺是抒情的现实主义。有花花草草、风俗饮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任中学国文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刊物。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底调至北京京剧团(院)任编剧。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 曾在海内外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汪曾祺全集》于1998年出版。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
【《汪曾祺说:我的世界》精彩书摘】
炒米和焦屑
小时读《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
说是自己家里炒,其实是请了人来炒的。炒炒米要点手艺,并不是人人都会的。入了冬,大
装炒米的坛子是固定的,这个坛子就叫“炒米坛子”,不做别的用途。舀炒米的东西也是固定的,一般人家大都是用一个香烟
【《汪曾祺说:我的世界》序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到处是河,可是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使船,走在乡下的架得很高的狭窄的木桥上,心里都很害怕。于此可见,我是个没出息的人。高邮湖就在城西,抬脚就到,可是我竟然没有在湖上泛过一次舟,我不大爱动。华南人把到外面创一番事业,叫做“闯世界”,我不是个闯世界的人。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着命运摆布。
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是在本城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已经写在《逝水》里。除了家、学校,我最熟悉的是由科甲巷至新巷口的一条叫做“东大街”的街。我熟悉沿街的店铺、作坊、摊子。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描绘出这些店铺、作坊、摊子的样子。我每天要去玩一会儿的地方是我祖父所开的“保全堂”药店。我认识不少药,会搓蜜丸,摊膏药。我熟悉中药的气味,熟悉由前面店堂到后面堆放草药的栈房之间的腰门上的一副蓝漆字对联:“春暖带云锄芍药,秋高和露种芙蓉”。我熟悉大小店铺的老板、店伙、工匠。我熟悉这些属于市民阶层的各色人物的待人接物,言谈话语,他们身上的美德和俗气。这些不仅影响了我的为人,也影响了我的文风。
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伞
高三时江阴失陷了,我在淮安、盐城辗转“借读”。来去匆匆,未留只字。
我在昆明住过七年,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前四年在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真是“囚首垢面,而读诗书”。后三年在中学教书,在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都住过。
一九四六年夏至一九四七年冬,在上海,教中学。上海无风景,法国公园、兆丰公园都只有一点点大。
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住的地方很特别,在右掖门下,据说原是锦衣卫值宿的所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五月,至汉口,在
一九五○年夏,回北京。在东单三条、河泊厂都住过一阵。
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我和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对农村、农民有了比较切近的认识。
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后住甘家口。不远就是玉渊潭,我几乎每天要围着玉渊潭散步,和菜农、遛鸟的人闲聊,得到不少知识。
我在一个京剧院当了十几年编剧。认识了一些名角,也认识了一些值得同情但也很可笑的小人物,增加了我对“人生”的一分理解。
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登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
我在这个世界走来走去,已经走了七十三年,我还能走得多远,多久?
一九九三年九月八日